刘剑锋:《书院门1991》——一个令人欣喜的收获
作家康铁岭长篇小说《书院门1991》出版后,作品研讨会曾分别在西安和山阳成功举办。毋庸置疑,《书院门1991》的问世是商洛文学乃至陕西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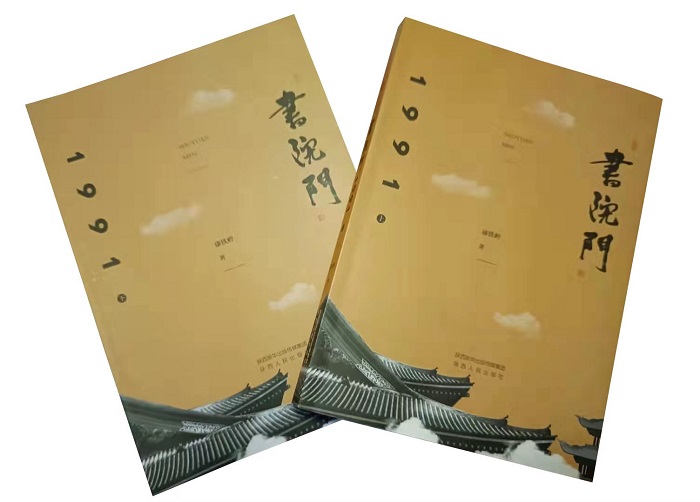
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市井生活的百态图
作者截取了古城西安一段特定的历史阶段,聚焦于古城西安一个我们所熟知的书画街——书院门,围绕一个来自华阳县的穷教师晏子敬,和同样是从小县剧团出来闯荡的女演员李雯的爱恨情仇,通过其周遭一系列来自不同阶层、不同生活与文化背景的人物,生动地展示出特定历史时期真实的社会风貌,淋漓尽致地把当时充斥于书院门的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描写出来,为人们记录了西安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真实生活与社会情态,画出了一幅难得的纷纭驳杂、厚重斑斓的市井画,为人们认知古城西安的历史脉络留存了一份珍贵的资料。
以市井为题材的小说创作无疑是一道别样的风景,具有重要的历史、社会、文化、心理认知价值和意义。在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传统中,市井生活是重要的书写对象。《红楼梦》是市井小说,鲁迅小说中的场景大多带有极强的“市井”性特点。而在当代中国文坛,市井小说也是佳作迭起。邓友梅的《烟壶》《那五》,陆文夫的《小巷人物志》,刘心武的《钟鼓楼》,贾平凹的《废都》《暂坐》等等,都是市井小说的代表。市井小说书写市井风俗民情,叙说普通人的生活与命运,展示的是不同人物特定时期的心态及其发展过程,折射的是特定时代的民族文化心理,显示了独特的审美取向。市井中的故事人物是构筑社会风貌的细胞,从市井中可以窥视到社会历史的原貌。市井小说常常肯定的是自然人性的存在状态及其价值,表现的是一种世俗化、地方化的审美情趣,其人物常常处于“灰色”的状态,即务实、逐利、圆通等市井心态,无涉高大上的理想愿景、精神追求以及终极关怀,因而更逼近社会、生活、人性以及人的命运的真实,具有极高社会认知价值。
康铁岭先生为我们描画的《书院门1991》的生活图景,以批判和审视的目光来描写书院门的市井风情、人物故事,以同情、批判、反思、讽刺甚至哀怜、忧郁相互交织的复杂情绪来叙事,不拔高,不贬抑,把古城西安当时可触可摸的真实生活、人物生活与命运展现出来,关注的是普通市井小民及其日常生活状态,呈现的是蕴含其中的风俗文化特征、内涵和审美情趣,艺术地再现了特殊时期的社会风貌和人的生存状态,因而,为读者认知西安提供了一幅难得丰富而形象的图画,具有极高的社会和文化的认知价值。
历史是一个长长的链条。市井是这个链条上最能够展现社会和人生风貌的因子和细胞。市井生活不仅仅是一种特定的民俗风物、社会情态,更是历史,是文化。以文学尤其小说的方式记录、还原、呈现、表现历史和历史中特有社会情态、市井图、人的生活与命运,揭示社会真实的状态与风貌,是写作者的使命与责任。康铁岭先生自觉地担负起来这个责任,在古城西安长长的历史链条上留下了一份记忆,实在难能可贵。
为我们塑造了真实可信的人物
一般写作者在长篇小说人物塑造中一般会出现两种状况,一种是按照自己的认知塑造出一堆理想化的、高大全式的人物,他们是真善美的化身,他们寄托着作者在现实中所无法企及的愿望,因而,他们往往只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与真正的生活无关,是高高在上的假大空;一种是陷于生活的真实而无法自拔,塑造的人物没棱没角,所有人都一个面孔,千篇一律,千人一面,鸡零狗碎,只是对周围人物简单的复制,扁平直白,没血没肉,苍白无力。前一种远离了生活,太假,太空,只是一厢情愿地自我倾泻和表达,文学的认知和表达能力不够,没有价值;后一种,陷于生活,缺乏塑造人物的艺术功力,同样没有价值。
而反观康铁岭先生的小说,他塑造的是我们身边的人,小说人物统统都是极为普通的市井人物,是“小人物”,但又是让我们感到陌生化的、各具血肉、各有情态、各有个性的人物。晏子敬、李雯以及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所有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不同生活际遇、不同生活与文化背景,他们是活生生存在于现实的人群。鲁迅先生小说中的“花白胡子的人”“二十多岁的人”,甚至全无特征的“所有喝酒的人”“喝茶的人”“女人们”“鲁镇上的人们”等等,他们构成一幅斑斓多姿的市井图画,其中蕴含的文化心理和社会哲学的意味极为深厚。康铁岭先生小说中便塑造了一大批这样的小人物,他们身上既刻下了社会转型期深深的烙印,又展现出市井人物特有的人性特点。
因此,康铁岭先生笔下的人物没有一个是完美的,没有高大上、真善美集于一身的“神仙”,也没有一个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魔鬼”,他们就游走于熙熙攘攘的人世当中,就是见怪不怪的身边人。他们既不“白”又非“黑”,是真实存在的市井小人物。
人是多么复杂的动物,集高级动物的思维、智慧、理智与低等动物的本能冲动于一体,因此这个世界上哪有神仙似的完人,哪有没有一点心智与良知的彻头彻尾的“坏人”?人是一个美丑、善恶交织在一体的混杂动物,而康铁岭先生恰恰就写出了人真实的复杂性、混合性。这些人物身上所展示出人性的假与真、美与丑、善与恶、矜持与放纵、理智与无羁以及情感与欲望、灵魂与肉体的博弈、纠结、盘旋,真实而富有质感地呈现出作为人本该有的复杂、混沌、本色与百态。这同样是难能可贵地把握住了文学作品人物塑造的真谛,值得肯定。
还有一点,康铁岭先生说过,他小说中的人物在生活中都有原型。就是说,他所塑造的人物都是他身边有血有肉有魂、对他触动极深的人,这样的人如何不鲜活生动?他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人物,而是把身边的人物写出来,这正如村上春树说过的,他说他的小说里的角色,都是在故事发展中自然形成的,不会事先决定“我要写出这样一个角色”。
为我们提供了可当做范本来读的小说语言
在商洛乃至陕西文坛,康铁岭先生不仅写小说,他是书法家。相比很多以充满语病、生造词和啰里啰唆、毫无节制的文字堆砌而成的个人消遣和自我陶醉的流水账式的作品,百万字《书院门1991》的语言却很简洁、生动、流畅。
高尔基曾经说了句大实话,但是说得非常到位:“文学创作的技巧,首先在于研究语言,因为语言是一切著作、特别是文学作品的基本材料。”语言犹如盖房子的建筑材料,质量不好,这房子不会好。
能够成为文学语言的底线和基本成色应该是,第一必须是规范的,不能生造词,不能有病句;第二不能看着眼熟,字句当中一看就是贾平凹的,是柳青的;第三必须是有棱有角,遣词造句中所体现出来的语言风格必须是自己的“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
贾平凹曾说:“悟性便是天才。”“有了悟性方能穷极物理。”康铁岭先生的语言悟性无疑是极高的。文学阅读让他触类旁通,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找到了自己的小说语言。他的语言干净,流畅,有质地,有温度,柔软、细腻、传神。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语言很感性,不矫揉造作,不扭捏作态,完全按照自己的语感来叙说,因而质朴自然,浑然天成。且他还能够把富有洛南地域文化特色的方言柔滑顺畅地融入到气韵通畅的叙事描写当中去,把生活中的俗语与文学语言的雅致很好地结合起来,一点也不显得生硬和突兀。这是真正的小说家才具有语言功力,是真正的小说语言,是可以让文学爱好者当做范本来读的语言。这也是这部小说能够立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告诉我们长篇小说可以这样来结构
《书院门1991》一百多万字。这么多的文字,对一个初写长篇小说的人来说,容易写得混乱,写成大杂烩,一锅煮,什么都扔进去,不讲结构章法,有头无尾,有骨头没肉或者有肉没骨头,最后取胜的仅仅是字数。
长篇小说的结构是对写作者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因为结构对于小说来说就是一个必须要构筑的合理、严谨又完整的建筑物骨架,骨架歪歪扭扭、设计不合理、不美观,这个房子是不会好的。因此,结构太重要了。韩东曾说“构造太重要了”,这个“构造”但非或不完全是建筑学的。红柯在新书《太阳深处的火焰》出版时说:“写长篇的关键是结构。长篇小说的酝酿期、构思期也很痛苦,作家基本处于傻瓜状态。”因此,处理结构问题,是一部长篇小说成败的关键。
但统观《书院门1991》,似乎看不到康铁岭先生如红柯所说的“酝酿期、构思期”的“痛苦”。或许早已取得显著文学成就的红柯,因为其极为丰富的创作实践,使他对自己的创作思考更多,追求更高,对自己要求也就高,思虑也就多,因而才会“痛苦”。但康铁岭先生便不是这样。他没有系统学过文艺理论,也没有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的尝试,因此,写起来脑子里根本就没有关于小说结构框框的制约和羁绊,完全可以按照想要的方式来写。
《书院门1991》以传统小说的时间线为基本结构,以晏子敬、李雯爱恨情仇为圆点为主线,以书院门为舞台,串联起了这个舞台上林林总总的各色人等,还有一个个由这些人构成的生动驳杂、活色生香的古城故事,他能够游刃有余地把这些庞杂浩繁的东西穿针引线地编织起来,并放置在合情合理又秩序井然的结构叙事中去,娓娓道来,脉络清晰,杂而不乱,有条不紊,从容不迫。这对于一个初写小说者来说是一个令人称奇的现象。但纵观这本小说林林总总的内容,会发现,其实生活本身以及用独特的眼光发现、存留、升华生活就是最好的结构。
康铁岭先生曾经在书院门开过多年的照相馆,接触的人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而且这些人物是深入到他的记忆深处的,于是“便决计把自己骨子里那些人和事写出来”。也就是说,他所熟悉的那些人和事是深入骨髓深处的,活灵活现,充满生趣,任何时候都呼之欲出,他不受小说创作条条框框的限制和掣肘,要做的就是像讲故事那样把它娓娓讲出来,鲜活的、特色各异的人和事不需要绞尽脑汁、搜肠刮肚地去编织、去构思便可以用文字道出来。因此,丰富的、刻进记忆深处的故事以及对此认知、体悟成了最好的结构。故事是什么?正如村上春树说过“故事就是存在于人们灵魂深处的东西,也是理应存在于人们灵魂深处的东西”。
正因为有了生活,善于讲故事的人便可以自然而然地把它生动而自然地讲出来。汪曾祺曾写过一篇《小说笔谈》的文章,在谈到结构时,他说:“小说的结构是更内在的,更自然的。”为什么会自然?丰富的生活积淀使然。村上春树说, “小说这玩意儿”只要想写,不必接受什么专业训练,也无须去大学念文学专业,差不多人人都能提笔就写。但是前提是必须有自己眼睛和心灵所能够记住的生活。康铁岭先生不仅仅在书院门生活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认知留住书院门生活与人物。
所以,这部小说一个重要收获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年过七旬的写作者的功力,这样的功力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够得到的,是长期阅读积累、反复历练才能够获得的。总之,《书院门1991》值得我们认真品读。
编辑 / 刘 佳 版权与免责声明


